青石铺就的长巷,飘散着古城淡淡烟火。斜顶,青瓦,红窗,妃色砖墙。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,像极了轻摇的蓬舟桨声。我的故乡,一个闻着风都可以做梦的地方,有一个醉人缠绵的名字,江南。
绿萝拂过衣襟,我默默彳亍着在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,把恍惚的记忆遗落在时光里。突然就诵起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姑娘,幻想着逢着那般结着愁怨的姑娘,及她走近,向我投来太息一般的目光。
在弄堂穿梭的丝丝风霜,静静躺在少女的梦里,像顾城说的那般:“我们扶着自己的门扇,门很低,太阳是明亮的。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”一曲碧水,一壶清茶,便是一下午的越调评弹。
那绵软而又不失腔调的吴侬软语,使生活和情感有了存在的可能。而城墙里,因为生活,因为情感,变得更加充盈丰满。
我能忆起的吴语,是旧城里的老折子戏。戏子穿着大红戏服咿咿呀呀在台上打转,唱着经年的梦回,转身拂去一行热泪。热泪转眼就跌进我的怀里,滚烫地让人方惊觉是一场梦。
我能忆起的吴语,是秦淮河畔灯火阑珊,佳人的自言自语。对红影,剪轩花。吴语便娓娓道来,那声音软糯缱绻,似一股清泉,又似三月的山花烂漫。
我能忆起的吴语,是空阶屐响,青石路尽头平添的轻柔歌声。浣衣女合着捣衣的节奏,伴着水花荡起的涟漪,空自浅吟低唱。

还记得那些青葱岁月里,九点的收音机准时传来用吴语播报的新闻,远在天涯的事似乎发生在这一刹那的周身。外婆踩着缝纫机,嘴中还絮絮叨叨着自我消遣。酒馆旁的老槐底下,妈妈轻摇着蒲扇,用熟悉的口音在我耳边叮咛着家常。现在想来,连蒲扇的清香都变得十分美好了。这一切不会吵闹,却比森林更有生机。
韦庄言: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。”
提到故乡,故乡又大概是什么呢?也许是食物,古人张翰出洛阳见秋风起,想起故乡的鲈鱼莼羹,于是回家去了。
我想起前不久的归家,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已久的馄饨和小笼包,突然惊觉,我思念的,我喜欢的,不是所谓故乡的食物,而是我吃惯的食物。乡音亦是如此。王小波曾记录到“老华侨回国,听见北京姑娘用正宗京片子骂人,又惊又喜,虽然被骂,也爽快得很。”
乡音,对身在异乡的异客一个多么奢侈的事物,它渗透进了骨髓成为了人的听觉本能,成为了另一个世界里的自己。我们思念的,我们喜欢的,不是所谓故乡的口音,而是我们听惯了的口音。
而我们想要回去的故乡,是我们习惯的故乡。恍惚间愕然,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春运火车票,而是一架时光机,一架能带我们瞬间回故乡的时光机。
乡音即是一架穿越时空的时光机,让每个异乡人瞬间返回故里,去寻觅被时光揉碎了的旧影踪。
如果有语文老师说乡音是一门艺术,有专家学者说乡音是一张历史的剪影。皆不置可否,只是在我的心中,乡音更是一种习惯。习惯了那个带着稚嫩口音的年幼的自己,习惯了从前的人和从前的事。这一种莫名的情愫,就是一种叫做“情怀”的事物,是用专业又科学的知识所无法表达的。从前不知,如今也不后悔知晓。
再回江南,酒馆摇身成了参天的高楼,老槐被人遗忘在了风里。收音机吱吱呀呀满是杂音,缝纫机也积了一层厚厚的灰,蒲扇被压在了箱底,甚至连故人也零星醉在了旧时光里。
十五从军征,八十始得归。
我多么害怕,我和吴语的故事就止于此了。但我又突然有了底气,因为一旦说起乡音,我还是那个静好岁月里最纯真烂漫的少女。
我庆幸,一旦说起乡音,我将搭上时光机,回故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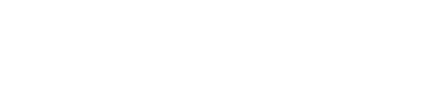 新闻网
新闻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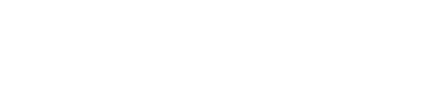 新闻网
新闻网